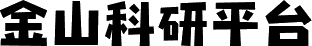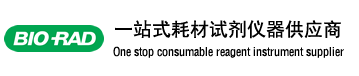缺席国家:韩国、捷克、埃及、南非、委内瑞拉等15国未再派领导人出席。
新增国家:印尼、马来西亚、伊朗、斯洛伐克等11国为首次派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。
持续出席国家:俄罗斯、朝鲜、柬埔寨、越南、老挝、巴基斯坦、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白俄罗斯、塞尔维亚、古巴、缅甸、蒙古国等。
缺席原因或外交背景
以下以“缺席”与“新增”两条主线,把2015→2025年之间外交背景最突出的几个国家逐一拆解:
一、2015 来过,但 2025 缺席的代表性国家
韩国
• 2015:朴槿惠顶着美国压力亲赴北京,当时中韩关系因“萨德”尚未全面恶化,朴槿惠想借历史议题拉近对华关系,也换取中国对半岛问题的支持。
• 2025:李在明上台后虽口头保持“一个中国”,但韩美同盟优先级明显回升——9 月 3 日前后,李在明先赴东京见日本首相石破茂,再赴美见特朗普,行程已排满,最后只派国会议长“降级”出席。首尔的外交考量是:
– 避免在中美之间再做“选边”示范;
– 对冲国内保守派“亲华过度”的指责;
– 美日同步缺席形成“集体立场”,韩国单独赴会显得突兀。
日本
• 2015:安倍政府以“国会事务”“安保法案审议”为由缺席,实质是党内右翼强烈反对“战败国首相出席战胜国阅兵”,担心国内选票流失。
• 2025:石破茂政府延续了“历史修正主义”立场,提前通过外交渠道呼吁各国“谨慎参与”,理由依旧是“活动过度聚焦历史、反日色彩浓”。更深层的动因:
– 担心国际舆论再次聚焦“侵略责任”,冲击其国内修宪、强军议程;
– 配合美国印太战略,降低中国主导的历史叙事影响力。
捷克
• 2015:总统泽曼坚持“历史不能忘记”亲自赴京,当时被欧盟内部视为“亲华异类”。
• 2025:欧盟对华整体氛围趋硬,美国施压“同步降格”,泽曼已不再担任总统,新政府亲欧远华,故缺席。
南非、埃及、苏丹、委内瑞拉等
• 2015 到场多因南南合作、中非合作论坛红利。2025 年:
– 南非:祖马下台后,新政府财政吃紧,与中国虽有合作但优先级下降;
– 埃及、苏丹:中东-非洲地缘格局变化,塞西政府需平衡对美、对以关系;苏丹在巴希尔下台后政治碎片化,无力派出高规格代表团;
– 委内瑞拉:马杜罗政权国际空间被进一步挤压,国内经济、政治危机叠加,无法成行。
二、2025 首次或时隔多年又来的代表性国家
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
• 佐科政府 2015 年因南海议题未派元首;2025 年普拉博沃刚上任,需要中国投资与市场,借历史议题修复政治互信,同时对冲美欧对印尼人权、棕榈油制裁。
• 安瓦尔政府一改前任对华“战略对冲”姿态,借出席争取“一带一路”旗舰项目东海岸铁路后续融资。
伊朗
• 2015 年因伊核协议谈判关键期,西方制裁未解除,不便“站队”;2025 年伊朗已加入金砖,又面临美以压力,借阅兵平台展示“向东看”战略。
斯洛伐克
• 2025 年菲佐总理刚完成选举,持“欧洲主权”“务实对华”立场,高调赴京意在争取中国电动汽车投资,同时与欧盟内部“对华去风险”声音拉开距离。
尼泊尔、马尔代夫、津巴布韦
• 都属“一带一路”早期收获国家:
– 尼泊尔奥利政府希望敲定中尼跨境铁路二期贷款;
– 马尔代夫穆伊兹政府刚上台,需平衡印度压力,借阅兵争取中国基建与安全合作;
– 津巴布韦姆南加古瓦则想为“债务重组”与“锂矿开发”铺路。
三、小结
• “缺席群”的共同底色:要么国内政治右转、历史修正主义抬头(日本、部分中东欧国家),要么受到美国同盟体系或欧盟集体立场掣肘(韩国、捷克、南非),要么自身政局动荡、经济困境导致外交议程降级(苏丹、委内瑞拉)。
• “新增群”的共同逻辑:均处于“一带一路”节点,或刚经历政权更迭,需要把“历史共识”转化为“现实合作”,在中美、中欧博弈中寻找新的杠杆或对冲空间。